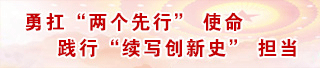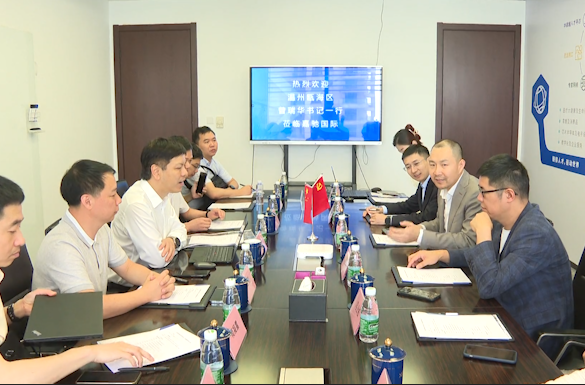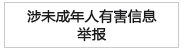压岁钱
2022年01月21日
■翁德汉
压岁钱是个奇妙的事物,在人生的长卷里占了好几个镜头。
对于小孩子来说,过年就是三件事情:吃好吃的、穿新衣服、拿压岁钱。压岁钱妙则妙在“压”这个字,而不是用。只要是“钱”,都能压住岁,无所谓大小,无所谓多少。
每年过年,我们都有压岁钱,只是金额大小不同而已。最早的几分几毛,到后来的几块几十块,都能压住岁。大有大的用法,小有小的去处,有的小孩子会急不可耐地拿去买玩具之类的东西,家长往往会说:“压岁钱要放三天不用,要不然明年就没压岁钱了。”于是小孩子只能从口袋里拿出钱币来看看,用手摸摸,不舍地放回去……

其实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,物资还是很缺乏的,压岁钱多了,也没有地方可用。印象里,我对压岁钱的多少毫无感觉。
我读师范的最后一个除夕,离十八岁成年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父亲可能没怎么有钱,我也没有期望能获得压岁钱,所以不惦记,只自己读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书。年夜饭后,父亲递来一张五十元大钞,说压岁钱还是要的。是啊,日子只要继续,岁还是要压的。我也没有狂喜,把这张五十元大钞夹到了正在看的书了,然后继续读了起来。
压岁钱,一般是长辈给小辈的,并不是说过年了,给你几块钱用用,而是寓意一种祝福,相当于一个护身符,保佑孩子健康成长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传统,在时代重压下渐渐消失不见,但是给压岁钱这一行为,却坚持了下来。这不是凑巧,也不是法律规定,而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。曾经和一个华侨在过年时一起吃饭,他背着一个包,看见亲戚家的孩子,就递一个红包过去,然后说:“好好读书啊,将来考大学。”亲戚乐呵呵地接过话说:“赶紧谢谢叔叔,来年读书拿奖状。”
压岁为什么用钱,而不是其他东西?在古代,钱的标志是铜板,具有辟邪的作用。在家里一些需要辟邪的地方,往往挂有铜板。当然,这也有其渊源,都和“钱”有关。而现代,人民币更是阳刚,所向披靡。一部小说里,说一个青年道士做法事,所用的法器,就是一张张百元大钞,一扔出去,一切邪物灰飞烟灭……
直接拿钱,总是有点不好意思,钱币外面的红包也就重要了起来。
过年时,妻子从网络购物平台买了一些红包,其中两种比较有意思。一个一看就知道是装百元大钞的,红包正面空出一个人的脸部位置来。我们把红色百元大钞塞进去,毛主席头像正好露在那个位置,直观又爆眼球。另一个正面是金元宝的图像,其中间空出格子,把百元大钞塞进去,“100”则嵌在里面,也比较有意思。
时代在进步,经济在发展,红包也一直在变化。在没有红包的时代,讲究一些的长辈用红色纸包压岁钱,端端正正的;随便一些的,就直接给纸币了。后来,薄薄的红纸做成的小红包,里面可以放一张,或者两三张纸币。而纸币的面额大起来了,红包也制作得大个起来了,纸张也厚起来了,各种符合人们心思的语句也印刷上去了。可以说,红包的变迁就是国民经济的变迁史。
儿子出生后,我的角色也变化了,以前是拿压岁钱,现在则是给了。在他还咿呀学语时,还不知道钞票为何物,我们就把压岁钱放在他的兜兜里。有一年突发奇想,打算把一元以上的纸币都准备一张,形成一套给他当压岁钱。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纸币倒容易取来,只是二元的纸币就难找了。找纸币在收藏圈是小事情,但对于我这样游离在圈子之外的人来说,就有点麻烦了。最终,也没能找到那张二元纸币,我打印了一张塞进去成一套,想来也是能辟邪的。
此后,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念头,都直接把百元大钞塞红包里给他。有一天,他说我做事不公平,给他母亲的压岁红包是八百元,而他却只有六百元。我说八和六这两个数字是有寓意的,妈妈的八百元,是期望她来年发大财,而他的六百元,则希望他“六六大顺”。他也听见去了,因为人总是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。

年前,妻子突然对我说少给儿子一些压岁钱,因为难忽悠了。我笑了起来。的确,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母子关于压岁钱归属的讨论。
儿子的外婆舅舅和阿姨每年都会送来压岁钱,如今更方便了,直接微信转账了。对于家庭来说,这些钱是小钱,但对于孩子来说,数目就不少了。在儿子还没注意到金钱的魔力时,以读书、买东西给他的理由取来了。上了初中后,突然就“聪明”起来了,说这是他的压岁钱,他的钱。他大概也意识到,这钱他保不住,说放他妈妈那里,但是必须给利息,每年计算一次……
对于压岁钱,我的记忆并不是遥远的童年时期。
在人生最无助时,过年了,我却躲在一个角落了,拿着手机接听各种电话。这些电话,并不是祝贺新年的到来,而是用极其不堪的言语想从我手里炸出一点钱来。一天三餐,是早早去食堂买来的肉包。人情冷暖,那段时间尽情地在我面前舞蹈。尽管咬着冰冷的肉包,但我从来不落泪,只是目光坚定地望着窗外萧瑟的树木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对过年有一种抵触感。
那一年,岳母让我们一家去瑞安过年,妻子和儿子已经提前过去。我在耗尽所有的精力后,坐着天天穿梭在温瑞平原上的十九路公交车,一路看尽繁华,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?当我风尘仆仆地在除夕夜赶到时,岳母递给了我一个红包,说是给我的压岁钱。接过来后,我悄然转身,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那也是我作为小辈,收到的最后一次压岁钱了。而后,我慢慢地走出来……
责 编:翁德汉
监 审:吴 远
总监审:周乐光

编辑: 陈奕如

- 2022/10/14第2092期 2022-7-1
- 2022/10/14第2091期 2022-6-29